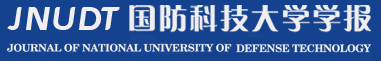摘要
直升机主减速器锥齿轮的动力学特性对直升机传动系统运行性能有直接影响。考虑传递误差、齿侧间隙等因素,采用集中参数法建立了弯-扭-轴向耦合的锥齿轮系非线性损伤动力学模型。为了获取损伤动力学模型中啮合刚度这一关键参数,提出了一种“切片式”直齿锥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计算方法,突破了传统势能法只能应用于圆柱齿轮副的局限,能够实现不同状态下时变啮合刚度的快速评估。通过对比不同状态下的模型仿真和实验结果表明,所建模型能够有效模拟锥齿轮系正常及故障状态下的动态响应特性,揭示系统故障响应机制与故障机理,为开发直升机传动系统健康与使用监测系统提供理论依据与数据支撑。
Abstract
The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elicopter main reducer bevel gear have a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the helicopter transmission system. Taking into account factors such as transmission error and backlash, a nonlinear damage dynamic model of a bevel gear system with bending-torsion-axial coupling wa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lumped-parameter metho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key parameter in the damage dynamics model, a slicing method for calculating the time-varying meshing stiffness of spur bevel gear pair was proposed, which broke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potential energy method that can only be applied to cylindrical gear pair and can achieve rapid evaluation of time-varying meshing stiffness under different states. By comparing the model simulation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t is shown that the established model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dynamic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evel gear system under normal and fault conditions, reveal the system fault response mechanism and fault mechanism, and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data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 helicopter transmission system health and usage monitoring system.
直升机具备卓越的机动灵活性和垂直升降的特点,能够完美地弥补各兵种在时间、速度、空间上的短板,成为立体战争中各种武器装备实现扬长避短、协同作战的关键纽带。锥齿轮系因其具有承载能力大、可靠性高、运行平稳、使用寿命长的优点被广泛用作直升机主减速器的动力输入端。锥齿轮系能够实现两相交轴线之间的动力传递,各向自由度间的力学耦合效应明显,啮合机理和所呈现的动力学特性相比传统的直齿圆柱齿轮传动更为复杂。基于整机质量控制和空间结构布置等因素的考量,直升机传动系统只能采用无冗余串联结构设计。直升机的飞行环境多变和飞行姿态频繁调整决定了锥齿轮常工作于高速重载、工况多变的恶劣环境中,齿轮系统容易产生疲劳故障,一旦出现故障不能及时维护或更换,将严重影响直升机飞行的稳定性与安全性。为了充分揭示锥齿轮系故障的产生机理,帮助及时诊断早期萌发的损伤和故障,有必要针对锥齿轮系开展损伤动力学建模研究与响应分析。
目前,国内外学者针对锥齿轮系的动力学建模方法开展了一些研究。任鸿飞等[1]建立了8自由度弧齿锥齿轮传动流固耦合动力学模型,利用分时迭代方法求解系统稳态响应。冉小平等[2]建立了7齿对齿面接触的斜齿锥齿轮有限元动态分析模型,分析了斜齿锥齿轮法向接触力的变化规律。Molaie等[3]研究了带齿隙的螺旋锥齿轮副的非线性动力学,从振动的角度阐明了重要的齿轮啮合内部激励。Liu等[4]面向航空发动机振动控制和故障诊断需求,建立了考虑时变啮合刚度、齿侧间隙、转速波动及转子不平衡激励的12自由度非线性动力学模型。Gou等[5-6]建立了考虑啮合刚度、载荷分配等时变参数的弯-扭-轴向耦合模型,研究了传递误差和驱动转速对系统非线性特性的影响机制。Pige等[7]提出了一种基于多个弹性基础的叠加并考虑了接触点弹性耦合的锥齿轮准静止态和动态仿真的啮合界面模型。Xu等[8]将非线性支撑特性引入锥齿轮传动系统中,通过构建8自由度动力学模型方程,分析系统的分岔与混沌行为。陈雪骑等[9]研究了疲劳断裂状态下转子-从动锥齿轮系统在复杂激励下的振动响应特性。李飞等[10]重点研究了变工况下摩擦因素对锥齿轮系统位移和啮合力响应的影响。
上述有关锥齿轮系动力学建模的文献大多侧重于仿真研究系统的动态特性,为锥齿轮系参数设计、动态性能控制等提供指导与依据,鲜有开展实验研究和涉及系统中存在故障的情况。此外,在建立锥齿轮系动力学模型时,有限元方法和集中参数法存在难以兼顾精度和效率的问题,集中参数法中齿轮副啮合刚度这一关键参数也过于简化。面向高端武器装备的智能运维需求,从动力学建模的角度深入探究直升机主减速器锥齿轮系的动态特性与故障机理,对直升机的状态监测、故障诊断乃至飞行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以某型直升机主减速器锥齿轮系为研究对象,采用集中参数法分别建立了正常及断齿状态下的非线性弯-扭-轴向耦合动力学模型;提出了一种“切片式”直齿锥齿轮齿根裂纹啮合刚度计算方法,并探究了裂纹扩展对锥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和时、频域故障响应特性的影响规律;最后采用台架试验验证了建立的锥齿轮系模型的正确性与有效性。
1 锥齿轮系损伤动力学建模
1.1 非线性动力学模型
图1(a)为直齿锥齿轮系三维模型,其主要几何参数如表1所示。锥齿轮副可简化为一对由弹簧阻尼单元耦合的刚性圆锥体,如图1(b)所示。力学模型包含8个自由度,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横向自由度x1和x2、纵向自由度y1和y2、轴向自由度z1和z2、轴向转动自由度θ1和θ2。δ1、δ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圆锥角,km、cm分别为齿轮副啮合刚度和阻尼,2b为齿侧间隙,b为间隙常量,e(t)为综合传递误差。

图1锥齿轮模型
Fig.1Model of bevel gear
为便于分析,将锥齿轮等效于图2所示的圆柱齿轮,由几何关系和运动分析可知,齿轮副的动态传递误差可表示为
表1锥齿轮系基本参数
Tab.1Basic parameters of bevel gear system

(1)
式中,xe1、xe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横向等效自由度,ye1、ye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纵向等效自由度,θe1、θe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轴向转动等效自由度,Re1、Re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等效圆柱齿轮的基圆半径。

图2等效圆柱齿轮模型
Fig.2Equivalent cylindrical gear model
等效模型和动力学模型的坐标之间存在转换关系,由图3可知
(2)
(3)
(4)
(5)
且由运动关系可知
(6)
式中,R1、R2分别为主、从动轮基圆半径。

图3坐标转换
Fig.3Coordinate transformation
将式(2)~(6)代入式(1)可得动态传递误差表达式为
(7)
锥齿轮副的动态啮合力Fm可表示[11]为
(8)

(9)
由受力分析和牛顿定理可得锥齿轮系动力学方程如下: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其中:m1、m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质量;J1、J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转动惯量;T1、T2分别为主动轮和从动轮的扭矩;齿轮副啮合阻尼常采用经验公式计算[12],ζ为阻尼比,取ζ=0.12。
1.2 直齿锥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模型
锥齿轮运动过程中,参与啮合的齿对数交替变化导致齿轮副啮合刚度周期性变化,成为引起齿轮系统振动的主要内因。时变啮合刚度是影响齿轮系统动力学响应特性的重要参数之一。
锥齿轮大小端的模数不一致导致了齿宽渐开线轮廓的渐变性,基于直齿圆柱齿轮开发的势能法应用于锥齿轮啮合刚度计算时存在局限性。为此,基于切片思想,将齿宽为L的锥齿轮轮齿等分为n段薄片,每段薄片i的齿宽可用dl表示,如图4所示。

图4锥齿轮轮齿切片模型
Fig.4Slice model of bevel gear teeth
“切片式”直齿锥齿轮副啮合刚度计算流程如图5所示。当切分数量n足够多时,每段薄片齿宽大小端的渐开线轮廓趋向一致,可以将每段薄片视为直齿轮。此时,只需计算每段薄片的当量参数,即可采用势能法计算每段薄片的啮合刚度。最后,沿齿宽方向将所有薄片啮合刚度进行求和即可获得直齿锥齿轮副的总啮合刚度,如式(18)所示。

图5“切片式”直齿锥齿轮副啮合刚度计算流程
Fig.5Calculation process for meshing stiffness of spur bevel gear pair in slicing method
(18)
由几何关系可计算分度圆锥角为
(19)
根据《齿轮手册》[12],锥齿轮分度圆直径d、齿顶圆直径da、齿根圆直径df、基圆直径db、锥矩Rzj可分别表示如下:
(20)
(21)
(22)
(23)
(24)
其中:δ表示锥齿轮锥角;ha、hf分别为齿顶高、齿根高,可通过齿顶高系数h*、变位系数X、齿隙系数c*计算获得。
(25)
假定Rrzj为分度圆齿宽某参考点锥矩,相关齿形参数可计算如下:
(26)
(27)
(28)
(29)
其中,mr、dr、hra、hrf分别为参考点模数、参考点分度圆直径、参考点齿顶高、参考点齿根高。
根据锥齿轮当量参数转换关系可得
(30)
(31)
(32)
(33)
(34)
其中,Zv为当量齿数,、、、分别为参考点处分度圆直径、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基圆直径的当量参数。根据上述参数即可画出等效直齿圆柱齿轮的齿廓线。
采用势能法对单段薄片啮合刚度进行计算,势能法推导过程仍沿用直齿圆柱齿轮结构参数,刚度模型进行仿真计算时采用锥齿轮薄片当量参数进行替换即可。
1.2.1 正常状态
图6为外啮合齿轮模型,该模型简化为从齿根圆开始的非均匀悬臂梁。齿廓包括三个部分:过渡曲线AB(A′B′)、渐开线BC(B′D)和齿顶线CD。

图6外啮合轮齿模型
Fig.6External meshing gear tooth model
根据弹性梁理论,啮合作用下薄片轮齿主要存在弯曲势能dUb、轴向压缩势能dUa和剪切势能dUs,其表达式分别如下:
(35)
(36)
(37)
其中:F表示拟合力;M表示啮合力对轮齿的弯矩;、、分别为薄片的弯曲刚度、轴向刚度和剪切刚度;E、G分别为弹性模量和剪切模量;dIx、dAx分别为x处截面惯性矩和面积,且dAx=2hxdl,。
由受力关系和渐开线、齿根圆角的几何特性可得弯曲刚度、轴向刚度、剪切刚度相关表达式分别为
(38)
(39)
(40)
其中,ρt表示齿根圆角半径,v表示齿轮材料的泊松比。
齿轮啮合过程中,轮齿会因接触而产生弹性变形,相应的赫兹接触刚度[11]可以表达为
(41)
此外,啮合力的作用还会导致齿轮轮体发生弹性变形,相应的轮体刚度[11]可计算如下:
(42)
由此,正常薄片的综合啮合刚度为
(43)
1.2.2 裂纹状态
裂纹损伤不会改变轮齿的齿形结构,但会减小轮齿的承载面积与惯性矩,削弱轮齿的承载能力,从而降低齿轮副的啮合刚度。假定裂纹出现在齿根位置且贯穿整个齿宽,深度方向为与中线呈γ角的直线,如图7中JK段。
据图7的草图关系,J点的坐标(xcs,hcs)可计算如下:
(44)
由此可得
(45)
(46)
其中,dcs为裂纹起点沿中线至齿根的长度。

图7裂纹轮齿模型
Fig.7Crack tooth model
根据裂纹不同的扩展程度,弯曲刚度和剪切刚度需加以讨论。本节以hte>hc>ha且α1>αc为例进行推导,其他情形的推导方式同理,主要区别在于根据裂纹几何位置确定截面积、惯性矩和积分范围。
hte、hc、ha分别为过渡终点B、裂纹终点K、齿顶点C至中线的距离。轮齿承载区的截面积、惯性矩分别为

(47)

(48)
将式(47)、式(48)代入式(35)、式(37)可得
(49)
(50)
因此,含裂纹故障薄片的综合啮合刚度为
(51)
分别将式(43)、式(51)代入式(18)进行求和,可得直齿锥齿轮副的总啮合刚度表达式如下:
(52)
(53)
2 锥齿轮系仿真分析
2.1 不同状态啮合刚度计算
假设锥齿轮系存在正常和主动轮裂纹两种状态。裂纹贯穿整个齿宽,起始点半径Rcs与齿根圆半径Rr的差值为0.5 mm、与中线夹角为70°,长度q分别取值0.5 mm、1.0 mm、1.5 mm、2.0 mm、2.5 mm直至最后变成断齿,用以模拟裂纹损伤的演化过程。仿真中锥齿轮系质量参数如表2所示。对于不同状态下直齿锥齿轮副啮合刚度,采用建立的“切片式”刚度模型进行仿真计算。分别设置齿宽切片数n为60、80、100、120、140、160进行试算,当n=100和n=160时锥齿轮平均啮合刚度差值小于5%。因此,综合考虑模型计算效率、成本和精度,选取齿宽切片段数n=100。
表2锥齿轮系质量参数
Tab.2Mass parameters of bevel gear system

图8为上述不同故障状态下直齿锥齿轮副的啮合刚度曲线。由图可知,正常状态下,双齿啮入和啮出时段的刚度基本对称。裂纹的出现降低了轮齿的承载能力,导致啮合刚度随裂纹尺寸扩展而逐步减小。由于裂纹出现在主动轮齿根部位,在转角较小时,轮齿刚进入啮合状态,此时啮合力臂较短,刚度受裂纹的影响较小。随着啮合过程的深入,轮齿啮合点逐步移动至齿顶部位,啮合力臂逐渐变长,裂纹对轮齿刚度的影响也逐渐增大,因此啮合刚度的减小幅度随啮合进程的深入逐步增大。当裂纹扩展至全部齿厚变成断齿故障时,双齿啮合区刚度因为主动轮轮齿的缺失产生大幅下降,单齿啮合区刚度则直接变为零。

图8不同状态下锥齿轮副时变啮合刚度
Fig.8Time-varying meshing stiffness of bevel gear pair under different states
2.2 动态响应仿真与特性分析
分别将7种轮齿状态下的啮合刚度曲线代入锥齿轮系动力学方程组,计算不同损伤程度下锥齿轮系构件的动态响应。假定主动轮转速为300 r/min,从动轮负载扭矩T2为32 N·m,锥齿轮系啮合频率fbm为90 Hz,主动轮转频fb1为5 Hz,从动轮转频fb2为2.5 Hz。
主动轮构件中心加速度响应的时域曲线和频谱如图9~10所示。由图可知,正常状态下时域曲线为简单周期运动,频谱由锥齿轮系啮合频率fbm及其高阶谐波构成。当裂纹尺寸小于1.5 mm时,裂纹对振动响应的影响并不明显,锥齿轮系的时、频域信号与正常状态较为接近。因此,当裂纹处于早期萌芽阶段,很难从时域响应的峰值脉冲和边带特征反映系统的损伤状态。
当裂纹扩展至1.5 mm,时域曲线出现了明显的周期性脉冲,啮合频率及其谐波附近存在密集的边带。当裂纹进一步扩展至2.5 mm直至断齿,周期性脉冲已经十分显著,边带幅值也随着裂纹扩展大幅提升。时域故障脉冲的时间间隔为Δt=0.2 s,对应脉冲频率为1/Δt=5 Hz,与主动轮故障转频fb1吻合。图10(c)~(e)展示了矩形框内频段的局部放大图,图中标注的5fbm两侧调制边带(5fbm-fb1、5fbm+fb1)间隔均为5 Hz,与时域响应反映的信号特征一致。

图9裂纹扩展对时域信号的影响
Fig.9Effect of crack propagation on time-domain signal of

图10裂纹扩展对频域响应的影响
Fig.10Effect of crack propagation on frequency-domain response of
综上所述,随着裂纹扩展的深入,锥齿轮系故障响应幅值逐渐升高,加速度响应呈现的时、频域特征都表明主动轮出现了轮齿故障,锥齿轮系损伤动力学模型的仿真结论与相关理论分析[9]是相吻合的。
3 实验验证
锥齿轮系故障植入测试在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的直升机传动系统诊断与预测实验平台上进行,其原理如图11所示。该平台由驱动电机、锥齿轮系、一级行星轮系、二级行星轮系、升速齿轮箱、负载电机等组成。

图11直升机传动系统诊断与预测实验平台原理
Fig.11Schematics of experimental platform for diagnosis and prediction of helicopter transmission system
为凸显故障效果,锥齿轮系故障植入类型选择断齿,综合考虑实验条件和装置承载能力,实验工况设置如表3所示。
表3实验方案及工况设置
Tab.3Experimental scheme and working condition settings

本次试验可分为基准测试和故障植入测试,基准测试假定锥齿轮系处于正常状态,将其作为故障植入测试的参考基准。断齿植入均采用线切割工艺完成,故障试件如图12所示。

图12主动轮断齿试件
Fig.12Test piece for broken teeth of driving gear
分别测试锥齿轮系基准状态和主动轮断齿两种状态下的振动响应,设置采样频率为25.6 kHz,每次测试时长为10 s。图13为不同状态下主动锥齿轮侧传感器测点2.5~4.0 s时段的加速度响应曲线。

图13锥齿轮系不同状态下的加速度响应
Fig.13Acceleration responses of bevel gear system in different states
由图13(a)可以看出,基准状态的加速度响应曲线整体波动较为平稳,无明显冲击,难以识别出信号的周期特征。图13(b)为断齿状态,轮系平稳运行阶段的加速度响应幅值基本相当,由于主动轮断齿损伤的存在,当损伤轮齿进入啮合区域时,图中出现了显著的周期脉冲,其时间间隔为Δt=0.2 s,与当前工况下主动轮故障转频一致。
对两种状态下的加速度响应进行频域对比分析。为消除测试过程中可能混入的多噪声干扰,采用功率谱方法抑制频谱背景噪声水平,结果如图14所示。

图14两种状态下主动锥齿轮加速度功率谱对比
Fig.14Comparison of acceleration power spectra of bevel gear in two different states
由图14(a)可知,基准状态下锥齿轮加速度功率谱中主要频率成分为啮合频率fbm及其高阶谐波(2fbm,3fbm,···),除此之外,啮合谐波附近还出现了一些幅值很低的边带成分。基准测试中出现边带现象在工程实践中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此时齿轮系统并非完美状态,系统可能存在某些不易察觉的材料缺陷或者制造误差,这些因素都将在响应功率谱中引起故障调制边带。断齿状态的加速度功率谱成分与基准状态基本一致,但其调制边带幅值明显大于基准状态(如图中箭头标注的主要异常区)。
图14(b)、(c)为50~105 Hz、230~300 Hz两个主要异常区的功率谱局部放大图,分别对应fbm、3fbm附近频段。由图可知,断齿状态fbm、3fbm两侧以主动轮转频为频率间隔的边带(fbm±Pfb1、3fbm±Pfb1)幅值显著大于基准状态。
图13和图14的时、频域特征说明锥齿轮系主动轮出现了轮齿损伤,符合实验的实际情况。同时,锥齿轮系基准和断齿状态的时域响应波形特征和频谱结构与仿真结果是一致的,表明本文建立的锥齿轮系损伤动力学模型能够描述系统不同状态下的动力学响应特性,验证了模型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4 结论
针对直升机主减速器锥齿轮系,本文开展了以下工作:
1)针对直升机主减速器锥齿轮传动的损伤动力学问题,提出了一种“切片式”时变啮合刚度计算方法,实现了不同损伤程度下直齿锥齿轮啮合刚度的有效计算;
2)通过动力学模型植入故障仿真,分析了锥齿轮系正常状态和断齿故障下的系统动态响应特性,数值仿真对比结果表明,损伤模型能够模拟锥齿轮的动态响应,有效地反映系统中的故障特征;
3)通过实验室环境下的台架试验验证了所建模型对于故障状态下系统动态响应特性模拟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本文建立的模型能够揭示锥齿轮系的故障机理,指导直升机主减速器的正向设计,为开发直升机传动系统的故障诊断算法提供理论依据和仿真数据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