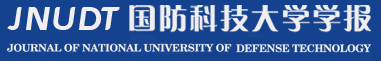摘要
数据驱动的通用气动分析模型可在任意工况下对任意外形开展实时可信的气动分析,是实现飞行器极速智能优化设计的关键技术。然而受“维数灾难”的影响,构建复杂气动外形强泛化分析模型的训练数据需求量极高,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应用。本研究主要针对数据驱动翼型与机翼极速优化设计方面的两项工作,通过对气动外形设计空间的合理表征,避开了“维数灾难”的不利影响,基于十万量级计算流体动力学训练数据构建了具备一定通用性的数据驱动气动分析模型,实现了相关气动外形的极速优化设计。
Abstract
Data-driven generalizable aerodynamic analysis models demonstrate strong capability in performing fast aerodynamic analyses under arbitrary aerodynamic conditions, which provides an emerging technology for intelligent aircraft design optimization. However, training generalizable analysis models for complex aerodynamic shapes requires a large amount of aerodynamic data due to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issue, which impede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this approach in the industry. Two tasks related to data-driven rapid optimization of airfoil and wing shapes were focused. By providing a proper representation of the aerodynamic shape design space, it effectively avoided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urse of dimensionality”. Demonstrations with approximately 100000-scale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training datasets were provided, which enabled fast aerodynamic shape optimization of airfoils and wings.
Keywords
飞机初步设计阶段需要开展气动外形极速优化,以快速考察不同约束和设计指标对性能的影响。然而,常规气动评估方法无法同时兼顾精度和效率,无法满足设计人员对高效可信气动评估与极速优化设计手段的工程需求。随着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技术的发展,深度学习模型与气动优化方法的交叉融合已成为飞行器设计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1-3]。中国空气动力学会理事长唐志共院士指出,“在飞行器气动外形设计上,传统方法强烈依靠专家经验,仅能针对特性构形,进行迭代优化设计,存在初始方案提出难、参数化设计局限多及气动设计耗时长等问题。AI的出现为气动设计带来了新的机遇,通过AI模型的高效、多样化并行能力,为气动外形方案设计提供了快速多样化灵活生成可能。”发展强泛化高精度的通用气动分析模型,实现任意气动外形在任意工况下的极速可信气动分析,是通向气动外形极速优化设计的关键技术之一[4],不仅在提升飞行器气动设计效率和鲁棒性、缩短高成本风洞实验测试周期、实现气动/结构/控制等多学科高效协同设计方面具有重大现实意义,还对推动AI与航空航天各行业科技创新与交叉融合、提升国家核心竞争力具有战略价值。其中一个可行方案是通过AI等方法进一步提高几何参数化的表征效率,另一个方案则是增强数据驱动气动分析模型的性能。
为了更进一步增强优化的效率和速度,就必须对现有参数化方法进行进一步的革新,降低它们的维度,提高它们的几何表征效率。模态参数化方法通过有效耦合设计变量实现降维。Robinson和Keane[5]验证指出,仅需少量模态即可完成二维翼型的参数化表征。Li等[6]和Allen等[7]的研究表明,基于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PCA)的翼型/机翼模态在气动外形优化中展现出卓越性能,其表现优于类别形状变换(class-shape transformation,CST)参数化方法和Hicks-Henne 型函数等传统参数化方法。与PCA模态不同,主动子空间方法(active subspace method,ASM)通过分析设计变量的输入空间,识别出对气动输出(如升力、阻力)具有关键影响的子空间方向,同时剔除次要方向实现降维。Li 等[8]将ASM与代理模型优化方法结合,在机翼气动优化中取得了比基于自由变形(free-form deformation,FFD)技术的代理模型优化更显著的效果。
随着流动大数据的涌现和数据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基于数据驱动的建模方法正在重塑流体动力学的研究格局。目前常用的降维数据驱动方法主要有本征正交分解(proper orthogonal decomposition,POD)方法。POD是一种从流场测量数据中提取基函数进行模态分解的方法[9],在获得高维非线性流动系统的降阶模型方向[10]和流场预测方向上表现良好[11]。该方法的进一步发展即为奇异值分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SVD)方法,其在降维与模态提取领域使用更加普遍。
目前学界在基于AI的数据驱动气动分析模型构建方面取得了初步进展,但整体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模型在泛化能力等方面仍较为局限。本文介绍了在翼型与机翼数据驱动气动分析建模与极速优化设计方面的初步研究工作,相关内容于2016年至2022年完成[12-14],作为一个侧影展现了机器学习技术在气动设计领域逐步得到深入应用的过程。
1 数据驱动的翼型气动分析与极速优化
飞机机翼、安定面和直升机旋翼叶片等重要部件都是由翼型沿展向分布构成,因此翼型设计对于飞行器性能至关重要。本节内容面向翼型极速优化设计需求,提出了一种数据驱动的翼型气动力评估方法,实现了任意翼型亚跨声速气动力的快速可信分析,并结合梯度优化算法开发了翼型极速优化设计方法。有关本节的详细研究内容可参见相关论文[12-13]。
1.1 翼型模态参数化
高效的气动外形参数化方法对于提升数据驱动气动力模型构建效率至关重要。为此,发展了一种基于线性正交模态的翼型参数化方法(以下简称翼型模态)。Masters等[15]采用SVD方法从UIUC(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翼型库提取了正交翼型模态,并开展了两千余翼型的重构复原实验,表明基于正交翼型模态的参数化方法在外形表征效率上显著高于CST、Hicks-Henne等常规方法。
SVD方法将一个高维矩阵分解成三个部分:左特征向量矩阵、特征值矩阵和右特征向量矩阵,具体形式如下:
(1)
式中,特征值矩阵是一个对角矩阵,其对角线上的元素值反映了原始数据的主要特征。通过保留占主导地位的特征值及其对应的左右奇异向量,可以将原始数据映射到低维空间中。
图1展示了从UIUC翼型库中提取的翼型模态,通常10多个模态即可高保真地表征翼型。除按照整条翼型曲线描述翼型外形之外,还可以通过弯度和厚度曲线导出弯度和厚度模态表示翼型。翼型弯度-厚度模态表征方法[12]与翼型模态的几何控制效率基本一致,尤其是模态个数大于10的情况下。然而,在翼型设计中弯度-厚度模态更为直观和有效。如图1所示,每个翼型模态都占有弯度和厚度信息,很难直接根据厚度约束选择合适的模态边界,而弯度-厚度模态则无须面对该问题,设计空间可以更紧致。最终采用了弯度-厚度模态表征翼型外形。

图1翼型模态
Fig.1Airfoil shape modes
跨声速翼型(如超临界翼型)具有与亚声速翼型不同的几何特征,因此采用专门的翼型模态分别对亚跨声速翼型进行参数化更为高效。UIUC翼型多数为亚声速翼型,因此可以基于UIUC翼型数据库提取亚声速翼型模态。NASA SC(2)系列包含21种不同厚度和升力特性的超临界翼型,可以基于该系列翼型提取跨声速翼型模态。亚声速模态和跨声速模态分别用于亚声速翼型和跨声速翼型的几何外形控制。
1.2 翼型气动数据采样与数据驱动建模
气动数据库是建立数据驱动模型(data-based model,DM)的根本。分别通过采用计算流体动力学(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CFD)计算构建亚跨声速气动力数据库:采用Python脚本自动生成翼型样本,采用PyHyp[16]自动生成每个采样翼型的CFD网格,采用ADflow[17]进行CFD数值模拟。其中,CFD求解器采用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Spalart-Allmaras湍流模型,CFD收敛指标为能量方程残差比自由来流下降15个量级。对于每一个采样翼型,自动记录其升力、阻力和力矩系数,并通过伴随程序计算并保存其对输入变量的导数信息。
在亚声速数据库中,翼型几何外形由14个亚声速模态表示,攻角范围为-2°到6°,马赫数为0.3到0.6。考虑巡航高度1万m的标准大气,根据马赫数变化,雷诺数在2.5×106到5.1×106范围内变化。在跨声速数据库中,翼型由8个跨声速模态表示,攻角范围为-1.5°到4.5°,马赫数为0.65到0.85,雷诺数为5.5×106到7.2×106。流动变量选取范围的确定标准为满足飞机典型巡航需求。需要注意的是,不论是亚声速还是跨声速,其数据库采样针对的均是小攻角状态。即对于大形变翼型可能出现的非定常涡等非定常效应来说,数据驱动模型尚未考虑相关情况。
为提高数据驱动模型的构建效率,使用基于流动变量和占优翼型模态的方法将采样空间划分为多个子区域,在每个子区域内采用拉丁超立方抽样(Latin hypercube sampling,LHS)方法生成一定量样本,并以增量LHS的方式生成新样本作为验证数据。实际构建过程中选择攻角和马赫数作为流动变量。占优翼型模态的选取是依据SVD后所得的各模态能量分布占比(即相应特征值分布)择优选取,能量分布越高意味着模态的相关性越强。子区域划分成功将对应的高阶模态边界进行了分解,通过子区域范围反向限制高阶模态边界。这样相比直接在全局进行拉丁超立方抽样,获取的空间更加紧致,模型构建效率自然更高。
由于翼型高阶模态的边界随占优模态的变化而不同,在采样过程中首先生成高阶模态的归一化系数,然后根据其上下边界计算其真实的模态系数。完成训练样本和验证样本的CFD模拟后,在每个小区域内开展模型精度验证,如精度不满足要求,则将验证样本添加至训练样本库,继续以增量LHS方法生成新的验证样本库,并重复以上操作。
最终构建了一个包含81 000个翼型样本的亚声速数据库和一个包含32 400个翼型样本的跨声速数据库,这些样本分别由16个和10个设计变量生成。一般来讲,基于CFD的梯度优化需要50到100次CFD和伴随程序的调用,因此构建这两个数据库的花费大概是翼型优化花费的1 000到2 000倍。后续验证可以说明,一旦数据驱动模型构建完成,基于该模型的外形优化设计可在1 s以内完成。
数据驱动模型为耗时的高精度气动力评估方法提供一个快速的替代方法。Kriging模型[18]是其中比较著名的一个,其训练是通过求解一个多极值问题,即最大化似然函数以确定最合适的超参数。这个过程需要反复对其中的相关矩阵进行求逆操作。而相关矩阵的规模会随着样本量或输入维度的增加而增大。当样本量或问题维度较高时,矩阵求逆变得更为耗时,因而训练模型变得较为困难。为了减轻这个问题,可以在模型训练中采用偏最小二乘(partical least squares,PLS)方法对问题进行简化处理,并利用梯度信息以提高模型精度,对应的代理模型称为基于偏最小二乘的梯度增强克里金方法[19](gradient-enhanced Kriging with partial least squares,GE-KPLS)。GE-KPLS方法可将超参数个数从问题维度降至1~3,可显著减少模型训练时间。但样本量过大的时候仍会受矩阵病态等问题的影响,因此单独采用一个GE-KPLS模型来处理一个包含十几万样本的数据库仍不现实。
而在高维代理模型领域,常用的方法主要有高维模型表示(high-dimensional model representation,HDMR)、降维代理建模(dimension reduction surrogate model,DRSM)、深度神经网络(deep neural network,DNN)。其中HDMR方法是最早被用于高维问题的高维代理模型[20]。HDMR与代理模型相结合,如基于克里金的高维模型表示(Kriging-based HDMR,Kriging-HDMR)方法、基于径向基函数的高维模型表示(radial basis function-based HDMR,RBF-HDMR)、基于支持向量回归的高维模型表示(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based HDMR,SVR HDMR)等方法,虽然获得了对高维输出响应的近似,但随着设计变量个数的增多,用于近似HDMR的低维代理模型个数也在快速增多[21-22],因此,HDMR仍是一种昂贵的高维代理建模途径。
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采用基于机器学习的多专家模型[23](mixture of experts,ME)构造数据驱动模型。ME是一种组合不同数据驱动模型的方法,能有效处理大样本、强非线性问题。ME基于“分而治之”的思想将原问题划分为不同子区域,在每个子区域内训练一个代理模型(专家)。这种策略极大地降低了单个模型中的样本数量,减缓了模型训练中相关矩阵病态的现象。首先根据流动参数将整个设计空间简单均匀划分为较小区域,然后在每一个小区域内采用聚类算法对几何设计空间进行自动划分。根据流动参数划分的小区域在亚声速和跨声速模型中分别为9个和12个。在每个小区域内根据ME的表现选用最佳的聚类个数。最终的亚声速和跨声速模型分别由108和72个簇类组成,在每个簇类层面基于GE-KPLS构建气动力子模型,并基于概率密度函数将子模型融合为统一的数据驱动预测模型。
1.3 数据驱动翼型气动分析模型的精度验证
图2展示了亚声速数据驱动模型对2 741个随机翼型的气动预测误差。左图中的散点图和箱线图显示了三个气动系数的绝对误差分布(箱线图正中的白线为中位数)。其中,86.6%的升力系数Cl误差低于1匡(0.001),99.6%的阻力系数Cd和63.8%的力矩系数Cm误差低于1匡(0.000 1)。图中显示的所有系数相对误差均小于0.3%,表明模型在亚声速区具有较高预测精度。

图2亚声速数据驱动模型的误差分析
Fig.2Prediction errors of the subsonic data-driven model
图3为跨声速数据驱动模型在989个测试翼型上的误差表现。阻力系数77%的误差小于1匡,最大为23匡;升力系数中有14个翼型误差超过10匡,但多数低于1匡;力矩系数有80.3%的误差低于10匡。三项系数的相对误差均低于1%。相比亚声速模型,升力、阻力和力矩系数的平均绝对误差分别增长3.2、8.9、6.7倍,相对误差增长1.78、2.23、5.03倍,源于跨声速区复杂流动及激波导致的强非线性,尤其对阻力与力矩影响更显著。尽管如此,跨声速模型总体精度仍处于较高水平。

图3跨声速数据驱动模型的误差分析
Fig.3Prediction errors of the transonic data-driven model
进一步对3个亚声速翼型(NACA4412、NLF1015、Clark Y)和3个跨声速翼型(SC2-0404、SC2-0606、SC2-0710)进行攻角范围内的验证(图4~9)。亚声速模型在马赫数Ma=0.45下的升力、阻力、力矩平均绝对误差为3.4匡、0.3匡、9.9匡;跨声速模型在Ma=0.73下的升力、阻力、力矩平均绝对误差为4.0匡、4.5匡、14.9匡。亚声速最大误差(2.3匡)出现在NLF1015翼型攻角为3.5°处,因ME将攻角划分为[-2.0°,0.67°]、[0.67°,3.33°]、[3.33°,6.0°]三段,误差常出现在分段交界。跨声速模型亦类似。总体看,数据驱动模型在全攻角范围内仍保持良好精度。

图4亚声速NACA4412翼型数据驱动模型与CFD对比
Fig.4Comparison of sub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for NACA4412

图5亚声速NLF1015翼型数据驱动模型与CFD对比
Fig.5Comparison of sub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for NLF1015

图6亚声速Clark Y翼型数据驱动模型与CFD对比
Fig.6Comparison of sub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for Clark Y(1)

图7跨声速SC2-0404翼型数据驱动模型与CFD对比
Fig.7Comparison of tran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for SC2-0404

图8跨声速SC2-0606翼型数据驱动模型与CFD对比
Fig.8Comparison of tran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for SC2-0606
1.4 基于数据驱动模型的翼型极速优化设计
非梯度优化算法如遗传算法收敛较慢,对于翼型优化需要万次以上气动分析,即便数据驱动模型可以进行快速气动分析,其优化效率仍不高,无法满足极速气动优化需求。而梯度优化算法在翼型优化中一般只需要调用100次左右气动分析,尽管多极值问题使得梯度气动优化问题受到一定质疑,但多数文献说明翼型优化是一个单极值问题[24-25]。因此采用梯度算法建立翼型极速优化框架,由GE-KPLS内置函数提供气动力梯度。在基于数据驱动优化过程中,气动分析单纯依赖数据驱动模型而不再调用任何CFD程序。

图9跨声速SC2-0710翼型数据驱动模型与CFD对比
Fig.9Comparison of tran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for SC2-0710
在马赫数0.45的亚声速区进行翼型优化设计,目标为最小化阻力系数,设计变量包括14个弯度-厚度模态与攻角,约束条件为升力系数和5个翼型厚度限制(x/c为0.1,0.3,0.5,0.7,0.9)。厚度下限基于NACA0012设定,优化翼型在各位置的厚度不小于其90%。为验证该优化问题是否为单极值,从50个Sobol采样点出发进行梯度优化,并比较其升力约束、阻力目标与设计变量act的收敛过程,结果如图10所示。图中红线表示50次优化的平均值,蓝线表示最大和最小值范围。结果显示,阻力系数差异在10-12量级,升力系数差异在10-10量级,表明所有初始外形均收敛至同一最优解,验证了该问题具有单极值性。

图1050个出发点的梯度优化收敛历史
Fig.10Convergence histories of gradient-based optimization starting from 50 different airfoils
图11为数据驱动优化和CFD优化的结果对比,Opt为优化后的结果,衬底的灰色阴影是通过绘制设计空间中的1 000个随机翼型生成,用来直观展示设计空间大小。对于升力约束Cl=0.5,两种优化方法的阻力系数差别仅为0.01匡。对于Cl=0.75的算例,如图12所示,两者的阻力系数差别仅为0.01匡,可见数据驱动的快速气动分析模型已足够精确,且数据驱动翼型优化都在1 s以内完成,可用于亚声速区翼型的极速优化设计。

图11亚声速数据驱动模型与CFD优化对比(Cl=0.5)
Fig.11Optimiz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ub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Cl=0.5)

图12亚声速数据驱动模型与CFD优化对比(Cl=0.75)
Fig.12Optimization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ub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Cl=0.75)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了跨声速区数据驱动翼型优化设计,并与基于CFD的翼型优化进行对比。与亚声速翼型优化算例类似,施加5个厚度约束,厚度约束值由SC2-0610翼型确定。为增加优化结果的鲁棒性,分别开展了翼型的单点优化和多点优化设计。图13为单点优化结果,设计点马赫数为0.72,升力约束为Cl=0.82,通过施加不同的力矩约束以考察其影响。总体上,两种优化方法的差别要比亚声速区大,不过阻力系数差别仍在2匡以内,升力系数差异在0.01以内。跨声速区减阻设计可得到一个超临界翼型,该翼型通过增大后缘弯度满足升力约束。不过这会带来负面影响,即导致翼型具有较大力矩,进而导致飞行器较大的配平阻力。该问题可通过在翼型优化设计中施加适当力矩约束予以避免。如图13所示,与无力矩约束优化结果相比,更严格的力矩约束导致了更大的翼型阻力。需对飞机整体气动外形进行综合优化设计才能更好地平衡两者影响,而该数据驱动模型能在翼型设计层面提供一个快速可靠的分析手段,对飞机设计人员提供一定帮助。

图13跨声速数据驱动模型与CFD优化设计对比(Cl=0.82)
Fig.13Airfoil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the transonic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Cl=0.82)
气动外形优化往往是通过削弱非设计点气动效率来提高设计点气动效率,因此单点优化结果一般并不实用。为了提高翼型设计的鲁棒性,还进一步开展了翼型的多点优化设计,优化目标是减小如图14所示的5个设计点下的平均阻力,力矩约束取为Cm≥-0.12,厚度约束设置与单点优化一样。施加升力和力矩约束的多点优化需要更多地调用数据驱动模型进行气动性能评估,对数据驱动模型的精度提出更大挑战。尽管如此,图15的结果显示基于数据驱动模型的极速优化仍然和基于CFD的优化结果非常接近,优化后的翼型形状几乎一样,除了激波位置有些许偏离,5个状态下的压力分布也几乎一致。阻力系数的差别在2.5匡以内,而升力系数和力矩系数的差别在0.03以内。这说明数据驱动模型在跨声速区也具备足够的精确性以应对多点优化设计。

图14多点优化的设计点马赫数和升力约束
Fig.14Mach numbers and lift constraints for the multi-point airfoil shape optimization

图15翼型多点优化设计结果
Fig.15Optimization results of multi-point airfoil design
2 数据驱动的CRM机翼气动分析与极速优化
2.1 机翼模态参数化
翼型设计领域拥有丰富数据(如UIUC翼型库),支持高效模态表征方法[12,15],以提升数据驱动气动模型构建效率。但复杂三维气动外形设计数据稀缺,相关模态化建模应用较少。因而,自动生成复杂气动外形并自主构建高价值气动外形数据库,已成为三维复杂气动外形高效参数化的研究前沿[1]。数据库构建需排除所有不满足约束的奇异外形,确保仅含气动性能优良的设计[14,26-27],避免随机采样带来的无效数据,导致难以提取有效低维模态[1]。
本研究利用多种深度学习模型处理翼型数据,建立快速通用的翼型奇异性分析模型[26-27]。数据驱动的翼型奇异性分析如图16所示,该模型可识别不同翼型的奇异程度,基于此施加外形约束,有效剔除高维机翼设计空间中的不可行域。进一步提出基于奇异性的约束优化采样方法,快速填充三维几何空间的可行域,构建机翼气动外形数据库[28-29]。在此基础上,采用SVD方法建立机翼外形的全局模态表征(见图17)。

图16数据驱动的翼型奇异性分析
Fig.16Data-driven analysis of airfoil abnormalities

图17基于数据库与数据驱动的机翼模态表征
Fig.17Wing database and data-driven modal parameterization of wings
为验证模态表征效率,采用伴随梯度方法分别在200维FFD设计空间和40维模态空间进行机翼减阻优化[28]。FFD空间与模态空间优化对比如图18所示,其中Cp为压力系数,两者最优外形高度一致,阻力系数仅相差0.3匡。表明该全局模态方法显著提升外形表征效率,可有效降低复杂气动外形空间维度约80%。

图18FFD空间与模态空间优化对比
Fig.18Comparison of FFD space and modal space optimization
2.2 机翼气动训练数据与数据驱动气动模型
CFD训练数据在60维设计空间内采样生成,参数包括马赫数、飞行高度、攻角、机翼不同站位的扭转角和50个机翼模态。为降低CFD采样成本,选择采用较为稀疏的机翼网格进行数值计算,该网格在气动外形优化设计方面的有效性已在前期工作中得到验证。为实现不同机翼外形CFD网格的自动生成,采用IDWarp[16]对基础网格进行变形处理。CFD数值模拟采用ADflow求解雷诺平均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湍流模型采用Spalart-Allmaras。部分数值模拟结果如图19所示,马赫数大于1.0的区域用灰色显示以凸显激波强度。

图19机翼样本的CFD模拟结果
Fig.19CFD simulation results of wing samples
从设计空间中选择训练样本的过程称为试验设计(design of experiments,DoE),通过采用多轮DoE策略可以逐步生成机翼样本数据,并在每一步构建数据驱动的气动分析模型并开展精度验证。与基于期望改进准则的自适应采样算法相比,这种多轮采样策略简单且稳健。在第一轮采样中,采用LHS方法生成初始样本集,并采用增量LHS方法生成验证样本集。在下一轮DoE中,将前一轮所有数据(包括训练集和验证集)作为训练数据重新构造数据驱动模型,并使用增量LHS生成新的验证数据集,重复该过程直到满足指定的精度要求。本研究共进行了五轮DoE采样,除了少数样本的CFD模拟未收敛,最终共得到135 108个训练样本和47 967个验证样本。
在数据驱动的翼型优化设计工作中,通过采用ME+GE-KPLS模型处理了包含十余万样本的大规模数据集,但该混合模型在不同专家模型的交界处存在函数不光滑问题。这在翼型设计中通常不会给优化带来问题,因为优化搜索通常由于几何约束而在同一专家模型范围内进行。然而,对于机翼外形优化设计问题,优化搜索跨越不同专家模型的情况更加常见,预测函数不光滑问题易导致优化失败。因此ME+GE-KPLS模型在机翼极速优化设计问题中并非理想选择。由于DNN模型具有拟合复杂非线性函数和处理大数据集的强大能力[1,30-32],最终选用DNN模型作为本研究中的数据驱动模型。实际上,即使在翼型设计问题中,后续研究[33-34]也表明DNN模型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对于DNN模型而言,通常情况下更多网络层数和神经元个数可提供更高拟合自由度,进而提升预测精度。DNN超参数对比如图20所示,图中对比了超参数(节点数Nnode和层数nlayer)对模型精度的影响,随着超参数个数增加DNN模型精度呈现先增高后降低的趋势。对于升力系数,当网络层数增加到6时,DNN模型训练易出现过拟合问题,模型在训练数据集上的表现虽更为精确,但在验证数据集上的精度并未提高。对于阻力系数和力矩系数的预测,网络层数分别达到5和4时出现类似问题。根据以上对比结果,分别选择了合适层数的DNN模型构建机翼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和力矩系数的预测模型,每层神经网络包含100个神经元。对于所有气动系数的预测,在47 967个验证样本中的平均误差均小于1匡。

图20DNN超参数对比
Fig.20Comparison of DNN hyperparameters
采用DNN单独对每个网格点压力系数进行建模比较困难,因此决定采用SVD方法对压力分布进行降维处理,通过对模态系数建模来重构机翼压力分布。为避免过拟合,采用了较为保守的DNN模型设置(3层网络,每层70个神经元)。如图21所示,数据驱动的压力分布预测模型几乎能给出与CFD分析相同的分布形态,表现出较高的预测精度。

图21数据驱动模型压力分布预测与CFD对比
Fig.21Pressure distribution prediction by the data-driven model and CFD
该数据驱动模型的采样稀疏度比率约为1.217,与1.3节翼型分析模型采样稀疏度比率(亚声速和跨声速模型分别为2.027和2.825)相比,有显著下降,不过这并未对本研究中的模型精度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升力系数、阻力系数和力矩系数的平均相对误差分别为0.20%、0.35%和0.36%,精度与翼型模型类似,采用该模型进行机翼优化设计有望得到与基于CFD优化设计相同的结果。
2.3 基于数据驱动模型的机翼外形极速优化设计
为满足机翼气动外形的极速优化设计需求,需要将数据驱动的机翼气动分析模型与几何约束模块[35]和梯度优化模块[36]耦合,建立数据驱动的机翼气动外形极速优化框架。该优化框架可同时考虑一个至多个(可达数千个)设计点与目标函数,以解决机翼优化设计中单点、多点、多目标等优化问题。数据驱动的机翼气动分析模型极为高效,在对47 967个机翼样本的验证测试中,总耗时为7.26 s,除去模型加载时间,每个机翼样本的气动分析仅需1/10 000 s。
采用序列最小二乘二次规划(sequential least squares quadratic programming,SLSQP)算法求解单目标优化问题,其中气动力导数由TensorFlow中自动微分功能求解。对于多目标优化问题,尽管进化算法可直接求解,但其在高维问题中效率极低,因此选择采用SLSQP开展一系列不同组合权重的多点优化设计问题来求解此类问题。不同组合权重对目标函数有不同侧重,可有效表示多目标优化问题的帕累托前沿线。
针对气动优化设计讨论组(aerodynamic design optimization discussion group,ADODG)案例4.1单点优化问题,采用该数据驱动模型开展优化设计,设计点巡航高度11 740 m,马赫数0.85,升力系数0.5,并施加一组厚度约束以保证有效容积。数据驱动的机翼优化设计在一个1.7 GHz CPU处理器上仅耗时33 s。而基于CFD的机翼优化设计在2.6 GHz处理器上需耗费18.4 h。图22为两种优化设计方法的结果对比,其中各点红色实线为基于CFD的优化设计,蓝线虚线为基于数据驱动的优化设计,尽管数据驱动的优化结果在翼尖附近仍有微弱激波,且升力系数与需求设定相差了0.003,但两个机翼外形几乎一致且具有相同阻力系数。数据驱动模型使得机翼优化设计提升了5 000倍,成本显著降低,几乎可实时地为飞机设计人员提供与基于CFD优化相当的机翼设计结果。
单点优化设计结果缺乏鲁棒性,工程实际中飞机机翼设计需要进行多点优化。如图23所示,对CRM机翼进行了九点优化设计,以进一步验证所发展的数据驱动优化设计方法,设计点和组合权重参照ADODG案例4.5进行定义。图24展示了优化后的机翼外形和其在设计点5(Ma=0.85,Cl=0.5)下的压力分布,同时与基于CFD的优化结果进行了对比,其中各点红色实线为基于CFD的优化设计,蓝线虚线为基于数据驱动的优化设计。可以看出,由于考虑了其他设计点下的气动性能,优化后的机翼在该设计点并非无激波,故此设计点的阻力系数相比单点优化有所增加。数据驱动的优化设计方法有效地捕捉了这种权衡,得到了与CFD优化相似的机翼外形,两者在大多数设计点的阻力系数差异不超过1匡。在优化耗时方面,基于CFD的优化计算成本为270核时,而数据驱动的优化设计仅耗时2 min。

图22数据驱动的机翼单点优化设计
Fig.22Single-point wing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the data-driven model

图23多点优化问题的马赫数和升力约束
Fig.23Mach and lift constraints of multi-point optimization
更进一步地,选择在双目标优化问题中验证数据驱动方法的有效性,目标函数为两个巡航状态下的阻力系数。结果如图25所示,数据驱动优化结果接近CFD优化求解的帕累托前沿线。基于CFD的优化花费600核时,计算成本极高,相比之下,数据驱动的优化仅需数分钟,阻力系数差异仅1~2匡。

图24数据驱动的机翼多点优化设计
Fig.24Multi-point wing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the data-driven model

图25数据驱动的机翼两目标优化设计
Fig.25Two-objective wing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the data-driven model
此外,使用低成本的数据驱动优化设计框架,可以新颖视角进行机翼设计。例如,通过执行一系列气动外形优化,可研究在不同高度和马赫数下巡航的益处。如图26所示,采用数据驱动优化方法可快速给出不同飞行状态下的最优机翼外形与气动性能,不同任务下外形优化的收益并不恒定(马赫数和飞行高度较高的任务中减阻效果更为显著),这种研究能为飞机设计提供快速指导,但如果使用基于CFD的优化设计,计算代价则会过高。
基于数据驱动模型还可以进行大规模多点优化设计,轻松平衡不同飞行任务的影响。如图27所示,使用数据驱动模型对441个状态进行了大规模多点优化设计。优化后的机翼与CRM机翼平均减阻为0.8 kN,虽然比单点优化更小,但这种折中优化降低了大多数任务中的阻力。

图26数据驱动优化给出的不同巡航状态下最优机翼外形
Fig.26Optimal wing shapes for different cruise conditions given by the data-driven model

图27数据驱动的大规模多点机翼优化设计
Fig.27Massively multi-point wing shape optimization using the data-driven model
3 结论
本文介绍了数据驱动的气动分析模型在翼型与机翼优化设计方面的研究工作,展示了深度学习算法在气动外形极速优化设计方面的成效与潜力。构建通用数据驱动模型虽可行,却面临维数灾难挑战,需严格筛选设计空间;采用数据驱动的模态化外形表征方法可有效缩减无效自由度,对提升气动预测模型的泛化性至关重要。在优化策略上,梯度算法因其显著提升收敛速度而适用于快速设计需求,非梯度算法则需谨慎选用。最后,该领域研究仍处于早期阶段,尤其需深入探索能够同时考虑机翼-机身等复杂外形耦合变化的快速优化设计方法。